纪昌兰|地方的宋代:巴蜀文化的政治再诠释
- 时事
- 2025-04-05 12:00:04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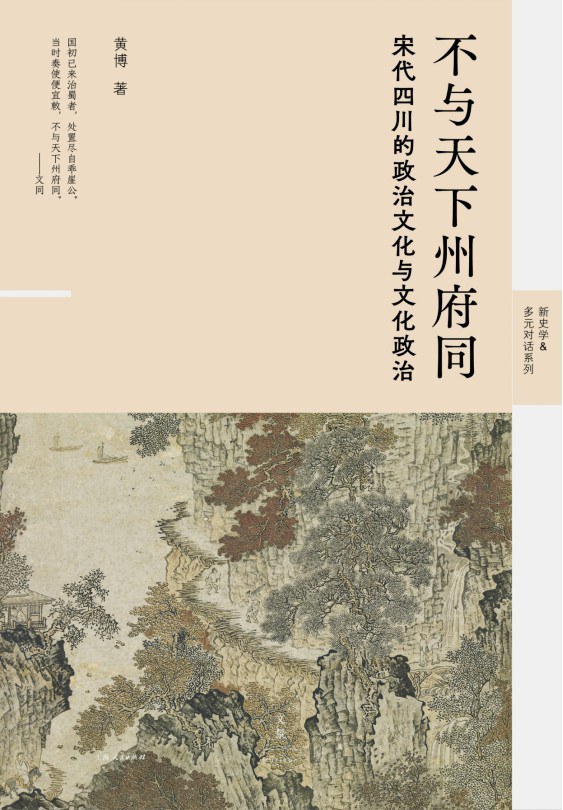
《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黄博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的独特气质早已深入人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及成都之际,有“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为世所艳称”的总体评价。这种侈丽繁华、民物殷阜的印象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人文意趣和丰富的文化景观,彰显了以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地区与众不同之处。出生和成长都在四川的四川大学青年学者黄博副教授所著的《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就是一部揭示和解析这一话题的专题论著。该著是其近年来从权力关系的文化形塑视角入手,以宋代四川地方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成果集成,也是学术界研究宋代地方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新成果。
一
作者从权利关系与地方政治实情切入,引领读者感受巴蜀浓郁的文化政治特色。全书以时间为经线,以地域风俗民情、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区域建置沿革、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互动、地方学人与学术风貌为纬线,描摹时空交织之下宋代四川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地方政治文化,编织出一幅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风景长卷。除绪言等内容外,正文凡十四章,各个章节自成专题,又相互联系。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围绕“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为主要议题,分章节专题阐述宋代多种权利在四川地方政治场域中的碰撞与互动,成都、重庆、泸州等四川所辖重要地区在宋代特殊民风民情背后所见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复杂建构过程,宋代四川地方学术风貌和本土学人的互相成就与成长轨迹等。本书立足于观察宋代四川地区的民情风俗及其显现出来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政治文化风貌,论述宋代四川政治与文化的诸多面象,展现时空交织视野下四川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和丰沛的历史文化资源。
两宋时期巴蜀地区“殷阜风流”的人文风情一以贯之,时有“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宋史·吴廷祚传》)的大致印象。如此看来,巴蜀确实“不与天下州府同”。作者正是抓住了巴蜀地区这种“特立独行”的政治文化风貌加以细细爬梳,将风俗、谣言、学人与学术融为一炉,揭示宋代四川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巴蜀学人历来以擅著史而闻名,注重历史的借鉴效用、精通考辨、体裁丰富等则构成了宋代四川发达的史学文化特色,诸多史学特色的背后贯穿始终的则是四川史学家们擅长运用史论这一独特的创作惯例和文化传统,闪烁着巴蜀史家以史论政的经世致用之隐意。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人文风貌,作者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士人,分别考察了宋代四川史家的前朝史研究及其以史论政的家国情怀、巴蜀史家张唐英注重挖掘历史场景中细节之处所见人物心理的历史心理学书写笔法、度正的政治生涯与学术交游、张俞及其在野参政、富民李处和儒商角色转换所见乐温在宋代的学术文化生态,选材对象涵盖了处于庙堂之上的精英到底层民间学人,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巴蜀地区的学人和学术,具象化考察巴蜀文化精英阶层的整体状态,呈现出活跃在四川地区在各个层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学人的文化生活日常,书写“活”的历史。
正如作者自述:“通过对宋代巴蜀地区民间学术文化的两个侧面的观察,试图打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联。”(页37)作者从整体出发,钩沉宋代区域社会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构建、互动过程,已经超越了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书写手法,立体化重现宋代巴蜀学人特有的人文风采,并由此揭示宋代巴蜀社会与文化的地方特色和政治文化意义。因此,作者以“人”为视角,赋予了宋代四川地区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以生命力和活力。
在考量“蜀人多变”这个在北宋朝野中曾盛行一时的说法之际,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弄清时人对四川的看法,就无法理解时人对四川的担忧”。因此,从各个层面详细考察宋人眼中的“巴蜀印象”就有了可堪考量的依据。北宋中期的大臣余靖有所谓“成都古之建国,其地险远,其俗富奢”的说法,引发了足以值得深思的巨大空间。具有这种独特的地域特点或许对于朝廷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险远”则意味着此地具有割据作乱的地理条件,而“富奢”就又意味着具有割据作乱的经济基础。余靖对于四川的这种印象在时人心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由此观之,巴蜀多变所涉及的层面,就不仅仅局限于“蜀人”了。
这样的特殊性无形之中强化了外界对于巴蜀地区的不安猜想,由此,关于巴蜀地区多变的种种意象和谣言乘势而起。面对这类谣言,包括中央和地方、朝廷与民间在内的各方势力都心存忧虑,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而“多变”这一印象或多或少也符合朝野上下对于这一地区保持高度“警惕”的时局判断,而朝廷对于蜀人的疑心之重亦可见一斑。也正因此,引发了朝野上下对蜀地、蜀人的戒备和密切关注。
北宋前期和中期,朝野对于蜀人多变的独特印象,是建立在巴蜀多变这一狡黠奇异的地域环境风貌基础之上的。川东的渝州在宋人眼中同样具有“地势刚险”的总体印象,地理环境之外时人对渝州风俗的看法与巴蜀地区属于“乱邦危邦”的判断遥相呼应。孔子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篇》)的说法恰巧符合宋人的渝州想象。宋代的渝州,背靠四川盆地(属于汉文化的腹心地带),而又面向世代居住于山林中宋人所谓“蛮荒”的族群聚居区。基于这种特殊的区域特色,渝州已然成为戎汉两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前沿阵地。
对此,作者也给予了特别关注,指出在宋人看来,这里是“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交融汇聚的重要据点,就西南夷诸部族而言,这里又是他们进入‘花花世界’的通道,还是他们可以进行掠夺的最方便的地方,所以渝州时常受到骚乱也不足为怪(页163)。如此特殊的戎汉交界地理位置,自然造就了渝州在地理和民族上的独特文化特色,促使此地成为宋代南方民族与汉族纷争融合不断的独特场域,演绎了一出出民族交流融合的精彩大戏,也使渝州在宋代焕发出别样的历史光辉,更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民族关系和区域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观察角度。
二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周边的环境产生着千丝万缕、或多或少的联系。或许作者正是秉持这一叙述原则布局整篇文章叙事的经线和纬线。论及魏晋以来巴蜀地区缺乏闻名于世的书法家,作者避开单刀直入的平面化叙述巴蜀地区人才辈出、文化气息浓郁的景象,而是抛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疑问: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书法艺术的发达乃是文化繁盛最直观的一种表现,然而自汉唐至宋,向来文学名士辈出、以文化繁盛著称的巴蜀地区,却偏偏罕见历史上闻名于世的书法家。其中的症结到底在哪里?作者以颇为独特的视角,从巴蜀地区的历史传承以及秦汉、魏晋、唐宋时代的文化传统讲起。娓娓道来,看似游离于中心,实则从各个角度全面考量,从本质上揭示巴蜀豪族大姓“财大气粗”的狂野文化气质与中原地区诗书传家的文化气质大相径庭。家风传承上的“异质”造就了巴蜀大姓与中原士族在家学上的落差,文化精英家族的没落和衣冠士族的缺失或许只是巴蜀地区书法欠佳的直接归因,而汉魏之后巴蜀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才是深藏于这种矛盾现象背后最深层次的关窍。类似埋下疑问的线索,细细耙梳之下步步为营的写作笔法在通篇处处可见。
作者的观察立足于宋代巴蜀的地域文化,而又不拘泥于巴蜀地域文化之一角;展现匠心独运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又积极与学界进行对话。在论及闽蜀同风这一独特的人文现象之际,作者一方面肯定前人所谓“两地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以及两地地狭人稠最为突出”这一人文地理因素造就的观点,一方面又不拘泥于此,另辟蹊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审思,指出宋代权力中心通过特殊化闽蜀地区,使两地在政治上被“特殊对待”显得理所当然,才是“闽蜀同风”论在宋代声势暴涨的根源,具有鲜明的个人观点。
史学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考证的严谨性,论述的客观真实性。作者在秉持这一治史原则的同时不忘以文艺化的灵动效果加以润色。全书体现出作者注重观察历史细节的细腻心思,这种心思既表现在对历史细节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对具体历史场景中人物心理的关注上。作者浓墨描摹了一位巴蜀隐士张俞的传奇人生。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隐士,对政治拥有巨大的热情,对自己理想的追求贯穿一生,属于不甘寂寞而热衷于功名事业、介于“小隐”和“中隐”之间的非凡“隐仕”。在分析他上书获得朝廷知遇而又拒绝入仕的缘由面前,本书铺陈颇多,从纵横两方面剖析张俞这种矛盾选择背后所蕴藏的“心思”。
拨开层层迷雾,“宋代是科举极盛时代,出仕不由科第则非正途,政治前途亦必黯淡”,“隐居待时,以在野之身参与益州本地政治,因其名重朝野,为地方官所敬,颇能左右一些地方政治的决策”,这是张俞以“隐仕”的身份参与地方政治的真实动因,实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类似种种勾勒,通篇可见。
从细节中发现历史,从心理上分析历史,知人论世。如此一来,读者很容易在作者精心勾勒的立体化历史场景中徜徉,仿佛穿越回千年以前的宋代,置身于或宏阔、或喧闹、或沉静的历史现场,跟随作者的脚步细细观摩“此时此景”,聆听历史的声音和回响,与千年前的历史真实和遥远的宋人产生同频共振的互动,置身历史,梦回千年。全书深入细致地呈现了以宋代四川政治文化为典型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于细微之处巧妙勾勒出中华文明在区域社会的发展及演变历程,内容丰富,考证严谨,文笔流畅,读来有一气呵成之感,颇见作者功力。
然而,宋代四川地区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与众不同”的独特性,还在于地域风貌和人文景象的“复杂性”。虽然巴蜀地区尤其是成都以“物阜民丰”“风流韵致”为典型的特质深入人心,但是俗语有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所展示的风土民情和人文风尚各具特色。受朝廷政策、民间文化、人群特质、地方风俗、时代变迁、自然环境、文化交流与融合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各个地区不同人群之间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和礼俗风尚难免充满差异,多重因素交织,使得宋代巴蜀地区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多姿多彩,充满地方特色和异质风情。宋人洪迈就有所谓“蜀峡山谷深复,鸷兽成群,行人不敢独来往。万州尤为荒寂”(《夷坚志·蜀梁二虎》的不同感观体验。巴蜀不同区域所见风土民情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似乎难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蕴含其间的人文地理因素、历史传承和区域文化因素、民族交流交融因素等都值得深入考量和挖掘。统观之下,考察巴蜀地区的独特性不能仅仅局限于成都、渝州、泸州、钓鱼城等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层面,期待作者后续更精彩的演绎。
下一篇:减脂土豆炒鸭血可食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