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伏瓦到伊藤诗织,女性文学能否成为独立的精神体系?
- 时事
- 2025-04-08 08:26:04
- 2
在最新出版的书评集《学坏》中,诗人、学者戴潍娜将女性主义理论锻造成认知棱镜,遴选出九位文字的刺客,从波伏瓦到伊藤诗织,从泰戈尔到林奕含,他们以反叛之刃划破蒙昧。她如猎手般敏锐,编织乔伊斯、赫胥黎与迪伦的思想脉络,剖析文本,让普希金的诗意与玛丽莲·弗伦奇的锋芒交汇共振。
戴潍娜,这位履历堪称“别人家的小孩”模板的优等生,那个硬要把人生轨迹拗成完美抛物线的学霸,竟扬言要“学坏”,像一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叛逆期。从规则里走出来的人,学坏的第一步不是放纵,而是自我赋权——从容地拆解秩序,重构属于自己的世界观。
鲍勃·迪伦是她的第一张精神切片。这位永不停息的艺术粒子,将存在本身熔铸为诗——在密西西比河畔的蓝调中栽种反叛基因,用棱镜取代民谣圣殿的彩窗,重塑艺术与道德的坐标系。他与父辈决裂,用音乐发出抗议,对一切不满的现实发声,但他也总在调戏我们,调戏世界。玩世不恭,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清醒?拒绝被定义,既是迪伦的姿态,也是他留给世界最重要的遗产。潍娜感叹:“至今,我仍觉得,这是我从迪伦身上学到的最棒的东西。创造,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情。人有权利随时创造自己!”真正的“学坏”不是叛逆本身,而是挣脱所有既定范式,让创造成为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
学坏的精神光谱上还有普希金、乔伊斯、波伏瓦、玛丽莲• 弗伦奇、伊藤诗织、林奕含、赫胥黎、泰戈尔,她以诗人的嗅觉捕捉这些“反派”角色骨血里的迷人气息。
觉醒,萌生于刹那间的怀疑。曾几何时,满心皆是无条件的信任、依赖与全身心的委身,直至那一刻,目光微微侧转,裹挟着质问毅然迈向叛逆之途。当学会 “学坏”,挣脱往昔的束缚,方得以真正以自我为灯,将世界的轮廓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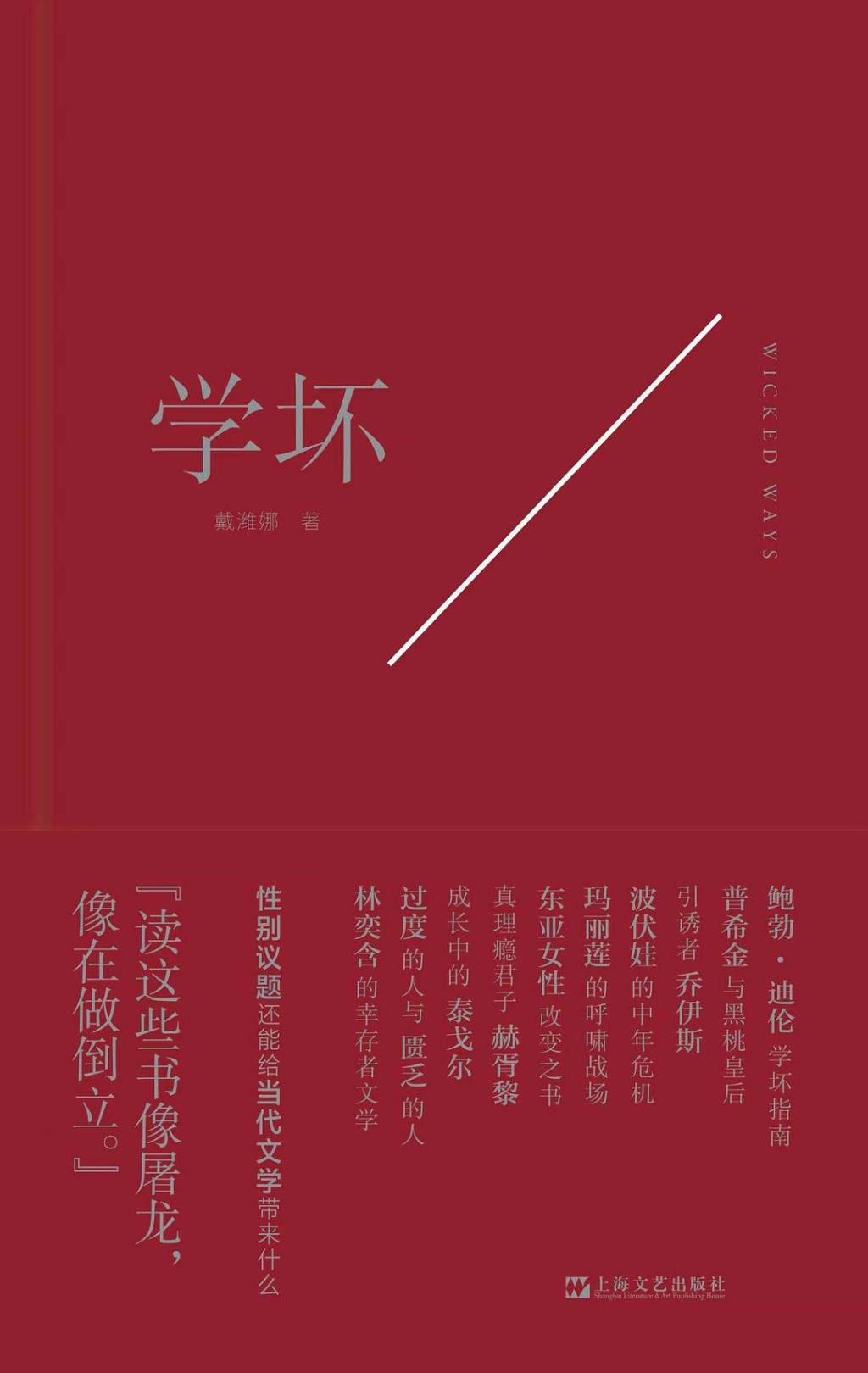
戴潍娜:《学坏》,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戴潍娜的学术佩剑刻着女性主义的徽纹,这位科班出身的理论者却鲜少策马冲入互联网的论战泥潭,更多地潜心于理论探究与文本钻研,似乎更愿意隐匿于理论与文本之后。或许是带有对网络激辩的怀疑与观念潮汐的警惕。正如波伏瓦曾高呼“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自己”,却未料到51年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女性子宫权益再度受限,如同被封印的恶灵重夺阵地。中年后的波伏瓦沮丧地发现,大半个世纪的女权斗争多以失败告终,早年的胜利只是一时假象,成果很快被遗忘。在《第二性》中她曾意气风发称“我们赢了这一局”,但在自传体回忆录终局篇改变了结论。对政权和人性的糟糕预判均已应验,面对并肩友人的变化也毫无伤感。这一切只能在文字中挽救夺回。她的书曾遭保守女性嗤笑,如今又因“缺乏斗志”被激进女权主义者不满。但她内心坚定,认为描写失败等并非背叛。
当伊藤诗织将山口敬之的暴行命名为“黑箱”,这个隐喻便成为刺穿日本司法沉疴的手术刀——在犯罪动机论主导的法庭上,受害者被迫承受着“二次强奸”的质询风暴。这位打破沉默禁忌的记者,用四年光阴在举证炼狱中淬炼出日本首例职场性侵胜诉案,却不得不在网络暴民的围猎中流徙他乡。她的《黑箱》不仅是个人抗争史,更是一份制度解剖报告:当瑞典的性侵救助体系已进化出创伤知情机制,日本司法仍困在昭和年代的认知泥沼,低强奸率假象背后是报案系统的结构性暴力。
与之形成文学共振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则以诗性文字解构性暴力的权力密码。林奕含笔下少女的幽微心绪,恰似照向施暴者的棱镜——当两本书不约而同地以文学反讽消解性侵者的身体神话,实则是用叙事手术刀为强奸文化实施祛魅术。然而诗织流亡海外的身影与奕含陨落的星芒,仍映照着东亚社会残酷的沉默螺旋:2010年日本三分之一的性侵案件仍在庭外和解中化为齑粉,那些未及书写的黑箱仍在吞噬着无数未名的晨星。
当舆论法庭将林奕含案锻造成“弱女文学”的十字架时,戴潍娜评论到:“林奕含同样花费众多文墨,描述了受害者在极度痛苦中,灵与肉强行割离的条件反射。这种‘心理休克状态’有时甚至会延续几天,以致延误报案的最佳时间。社会对完美受害者的期望,显然是严重缺乏常识和同理心的。她们在侵害发生之后,选择继续漂亮地生活,就是最大的英雄主义。”受害者有选择,可放下也可铭记,因没人该被如此对待。受害者不都有打破沉默的义务,也并非要有如诗织和林奕含般成就才算英雄,被侵犯时更不必以死相拼。
面对进步的观念,戴潍娜所担忧的并非女性权益的增长,而是女性主义在近年来对外在权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女性自身生命经验和价值体系的构建。结果,在政治与文学等领域,女性未能创造出独立于男性普世价值之外的新范式,而是不断适应甚至延续既有的男权体系。在政治领域,女性领导者往往表现出“比男人更男人”的姿态,依附于传统权力逻辑,而未能真正开创具有女性气质的政治模式。同样的问题在文学领域亦然,“女性文学”仍被定义为“女性创作的作品”或“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而缺乏对其独特美学、语言体系和思想内核的更深层辨析与探索。
此外,女性主义的斗争方式也陷入了性别对抗的二元结构,过度专注于话语权的争夺,使其成为另一种倒置的权力系统,最终缺乏想象力,陷入简单的性别战争,而未能提出真正超越性别对立的思考与可能性。
戴潍娜在剖析女性写作时揭示,女性文学传统的建立不仅是对女性创作的整理与归纳,更是一场深刻的颠覆性实践。它要求我们回溯女性在历史中的整体处境,并理解性别不仅关乎身份认同,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方法论和行动体系。真正的女性文学传统不应只是对既有文学史的补充,而是对世界建构基础的反思与动摇——它质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解构主流叙事,甚至推动历史的重写。正因如此,这种颠覆性往往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甚至遭遇排斥与抵制。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挑战与抵抗中,女性文学才真正拥有了塑造自身传统的可能。
那么,我们赢得这一局了吗?女性文学是否真正摆脱了男权价值的规训,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体系?我们是否已经拥有足够的语言来承载女性的历史、经验与思考?或许,这场战役远未结束,但每一次书写、每一种新叙事,都是在推进这场漫长而必要的博弈。答案尚未揭晓,但至少,我们仍在棋局之中。
上一篇:公务自行车押金退还政策解析
下一篇:二年级奥数难度适中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