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污染土壤跨区转运集中修复:多重机制创新可借鉴
- 社会
- 2025-04-13 10:24:07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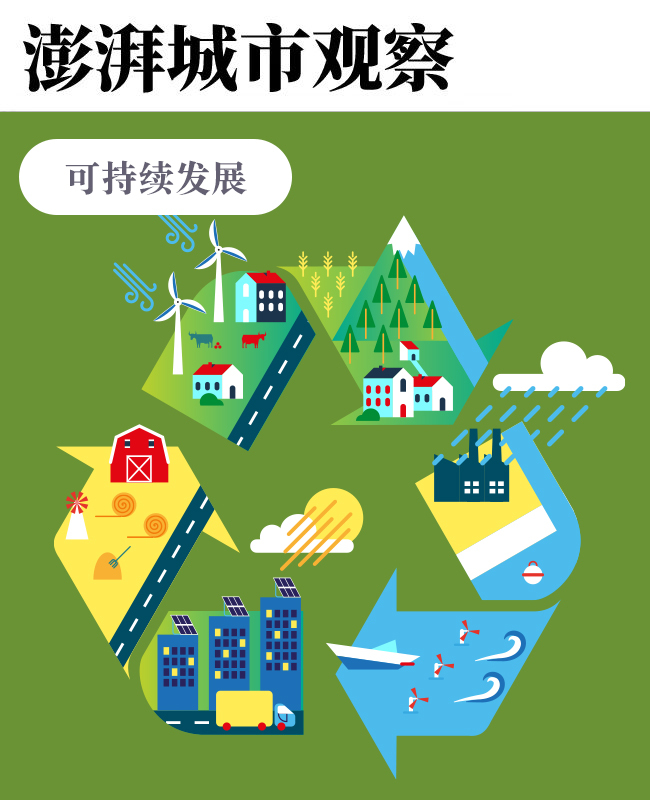
上海首个污染土壤跨区转运项目正在宝山的南大土壤修复工厂进行。该项目自2025年初启动,已完成大半,近3.3万方有机物污染土壤要从浦东新区某“城中村”运此修复后再运回原处。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正有绿色创新的机会。《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土壤法”)明确,对于污染超标的地块,土壤修复是开发利用的必要前提。上世纪末,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等小企业和作坊主要分布在宝山、普陀、杨浦、浦东和原闸北等区。城市多年扩张后,这类尚待土壤修复的预备开发地块,如今或处于城市副中心周边,附近已有各种建筑设施。修复土壤又需在原有土地之外占用大块地面。由此,转运污染土壤,在异地集中修复,可令土地使用权人更有效率地利用土地,更快完成开发,同时避免重复工程建设。南大土壤修复工厂,正以此模式修复宝山老工业区的污染土壤。另外,由于各区属地管理,存在责任划分等问题,污染土壤往往难以跨区转运。2025年初的跨区转运项目之所以能够实现,也是各方协同市、区的生环部门和沿途交通部门等,并运用信息技术,在监管闭环上实现了突破。

南大土壤修复工厂,正在对跨区而来的污染土壤进行异地集中修复,修复完毕后会闭环运回原地。 王昀 图
上海建工与宝山南大开发公司共同成立的南大土壤修复工厂,究竟是如何启动运作的?在污染土壤异地异位集中修复治理的实践中,不同部门如何合作,有哪些技术和管理模式的突破?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在2025年2月-3月走访了南大土壤修复工厂,并访谈了上海建工环境科技公司、宝山南大开发公司的工程师,以解答上述问题。
前瞻性的试点与合作
法律法规的压力是最为首要和关键的。中国的土壤污染治理也经历了长时间探索。这也构成了这项实践的背景。
中国首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出台于1995年,直到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才有了首个系统的行动纲领。而前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世纪初遗留的土壤污染,因经历了国企改制、工厂倒闭等诸多复杂过程,难以追溯土壤污染人,需要让后面的土地使用权人负责。根据2019年施行的土壤法,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地块,若要作为建设用地,必须进行土壤调查,倘若其污染物超过管控标准,则必须依据评估报告完成风险管控和修复,之后才能进行建设。上海市则根据实际情况形成了具体操作规定。如2024年10月发布的《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实施办法》与《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相关活动弄虚作假行为调查办法》等。
接下来,是结合区域转型的实际考量,为土壤修复创造条件。南大土壤修复工厂之所以成为前瞻性的试点,得益于十多年来宝山相关各级部门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敏感性。
建立南大土壤修复工厂是为了本区域的土壤修复,更好地服务于南大地区开发建设。南大地区在2012年被列为上海五大整体转型区之一。2012-2014年宝山南大地区综合整治过程中,已有“生态建设先行”意识,结合当时的拆违,调查摸排了过往工业企业,准备后续做土壤治理和地下水治理。2017年,宝山南大地区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污染土集中处理中心成立,面积有48000平方米,也成为当时国家环保部城市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工程技术中心的污染土修复示范基地。2019年土壤法施行,恰逢南大地区面临控规调整,宝山以规划地块边界范围——敏感性用地与非敏感性用地对应不同的土壤修复指标,做了全面的产业调查,判断后续需要修复的土方量较大,原有基地面积不够用。由此,南大地区综合改造指挥部结合正进行的富国皮革厂土地征收,申请保留一部分厂区用作土壤修复基地。基地扩建到大约74000平方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场地、技术等各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协调和突破。包括租金的免除和对原场地设施的保留等。
2020年6月,宝山南大环境治理技术服务中心揭牌,由上海宝山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上海建工集团下属环境科技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前者给予优惠政策免去租金,后者提供技术负责对整个中心进行运营。上海建工集团投入高效率、一体化的专业设备,如分离重金属的淋洗设备、针对有机物的氧化设备和脱附设备等。目前,南大土壤修复工厂的年处理能力为15到20万立方米,第二阶段产线投用后,最大年处理能力可达45到60万立方米。按照后续规划,土壤修复工作结束,这片地会成为公共绿地。

南大土壤修复工厂中,保留下的原富国皮革厂四车间,在土壤修复工作中继续使用。 王昀 图
土地租金的免除对土壤修复工厂意义重大。按照宝山区政府指导价,一天一平方米需要1.2元,而土壤修复难以负担这样的成本。另外,原本土地的划转和出让,需要进行“四通一平”。但因为运营和建设开发合作紧密,协调得力,原厂区有三个车间得到保留,地坪进行翻浇,直接用于土壤修复基地。这也得到了宝山区政府支持。工程师们认为,老的生产车间结构稳固,比自己再进行钢结构搭建更有优势,还可避免先拆再建的二次投资。这无疑也为绿色做了直接的贡献。
异地集中修复:从服务本地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基于所处的不同环境,污染土壤修复有诸多路线方法。相比其他地方采用固化路线,上海更偏重氧化、淋洗和热脱附的成熟工艺。南大土壤修复工厂采用的方式,也是由上海土壤污染的特性而来。上海是典型的淤泥质土壤。土的表层是建渣(construction waste);而在两三米之下,土的颗粒就会很细,导致污染物一旦吸附就很难去除。对此,技术团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针对粘性土壤重金属的专利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其设置的修复设备,又针对上海不同区域土壤的粘性特点进行针对性改良,使得修复效果更好,产能更高。
概括说来,针对土壤中的有机污染,如各种烃类,会进行化学氧化处理,即加入氧化药剂,将污染物降解掉。如果有机物浓度超过国家标准限制10倍,则采用热脱附工艺,让土壤中的有机物在高温状态下变成气态,将收集到的气体在末端脱硫脱硝。而上海地区污染土壤常见的类型是重金属污染,如六价铬和铅砷汞等,在退产企业和仓库比较常见。对此,土壤修复最常进行的步骤,是类似洗衣服,把药剂和土壤拌在一起,通过强力的物理搅拌,使土壤里的重金属以水相形式脱离出来,也即淋洗工艺,再进行后端处理。如果土壤是复合污染,就要先后进行这两段针对性的工艺。

南大土壤修复工厂中,正在运转的土壤淋洗设备。 王昀 图
由此,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服务上海的不同区域。 以其具备的产能,南大土壤修复工厂可服务宝山以外的项目,现阶段也在探索跨区域修复。土壤法规定,如要转运污染土壤,则包括运输的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都需要提前报给所在地和接收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如今在上海市,污染土壤跨区转运已有突破。根本上,政策的突破意味着承担风险,监管方法也需要有一定更新;运用技术手段,可以明确责任,避免扯皮推诿。实践中,为避免干扰交通等,土方转运要在半夜进行。而作为施工单位,土壤修复工厂要提出方案,使相关方面了解在转运过程和施工过程中,如何保证每一方土能够进到修复工厂并顺利返回。涉及的技术问题包括,用摄像头对进出场的车牌进行识别和记录,确保车牌在审核过的名单之中。如果是陌生车牌,信息就会通过平台传送到管理人员手机上。出场后,司机必须按照事先规划和申报的路线行驶。车辆如果出现偏离和等待,也会进行预警。倘若偏离,会从全程车载监控进行反向追查;如果等待,距离最近的服务点会进行情况核查。倘若路上抛锚或小剐蹭,就要启动审批过的应急方案。如果路上颠簸导致污染土掉落,就要用到车上的应急处置包,包括铲和密封袋等,确保不会影响市政道路。这些路线也对沿途交警大队报备过。抵达工厂后,也有摄像头识别车牌是否对应,其系统对接到生态环境局。同时还需核对车辆信息和车重,是否与出场时对应。车子把土卸完之后,返回之前,要再过一遍重量。
考虑到空间距离,宝山南大土壤修复工厂本身的辐射范围有限。工程师们认为,这种模式本身可供更多地方参考。他们也在积极和大连等城市合作,进行化工厂迁出后的土壤修复。各地也在探索自己的方法。比如,广州也有污染地块土壤异地处置异地修复的做法,但与上海相比,修复后的土壤不需要再运回。这无疑是为开发建设带来方便,但也显得有些激进。
既有的创新可以带动未来的创新。土壤法虽然规定严格,但也提出地方要探索新型的土壤修复模式。南大土壤修复工厂也在其他路径上做出探索。比如,工程师们也在推进,针对工业区内部在产的化工厂,进行局部修复。比如修复管道泄漏造成的土壤污染。如果能在早期把这些工作做好,相比最后大规模修复,环境和资金成本相对都会更低。
(感谢南大开发公司工程建设部尹俊、综合协调部吴莎;上海建工环境科技工程事业一部郭振海、胡一鸣)
-----
城市因集聚而诞生。
一座城市的公共政策、人居环境、习俗风气塑造了市民生活的底色。
澎湃城市观察,聚焦公共政策,回应公众关切,探讨城市议题。
















有话要说...